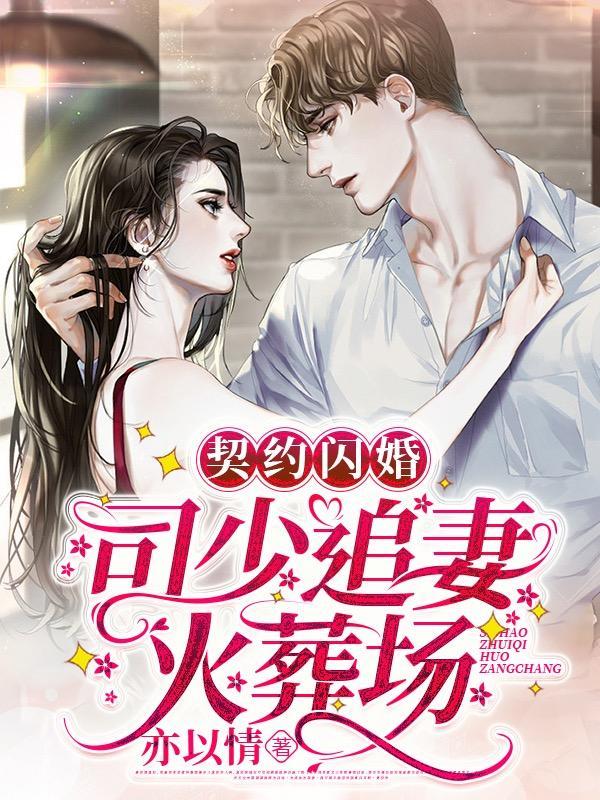366小说>朕这一生,如履薄冰 > 第382章 双刃剑呐(第2页)
第382章 双刃剑呐(第2页)
而是应该以客观需求为准,以实际效能的角度去出。
比如廷尉,被先帝老爷子改成了大行,在历史上,又被后来的汉武大帝改回为廷尉。
意义在哪里?
无外乎就是孝景帝觉得廷尉不好听,武帝爷又觉得大理更不好听而已。
而在留荣看来,像‘朕觉得不好听’这种改换九卿名称的理由,其实是很没必要的。
一个九卿属衙,如果要改,那就改他的权责范围,改他的效能;
改完之后,再看原本的名称,是否与改革过后的效能、职责相符。
好比廷尉,被历史上的景、武爷儿俩来回改,改来改去,无论是叫廷尉还是大理,终究还是没改变这个部门,是作为中央最高司法机构的职能。
故而,改这个部门的名称,是完全没有意义的。
——景帝改廷尉为大理,没有意义,纯闲的;
武帝又把大理改回去,更没有意义,更是闲的淡疼。
所以,对于过去的廷尉、如今的大理,刘荣的态度很明确。
既然已经改了——既然已经无意义的白忙活了一场,那就不要再无意义的多忙活一场,把名字再给改回去了。
有这精力,干点别的什么不好?
同样的道理——奉常既然改叫了太常,那就这么叫着吧;
典客还没改叫大行,那就不改了——即不改为大行,也不改为大鸿胪。
宗正不改宗伯,郎中令不改光禄勋,一切照旧。
把有限的精力,都放在有意义的事儿上,而非这种脱裤子放屁——多此一举的事儿上。
当然,这也并不意味着刘荣,完全不认可历史上,生在景、武二朝的九卿名称、职权大洗牌。
尤其是原历史时间线上,汉武大帝针对内史的拆分,刘荣非但不觉得不好,反而还十分赞同。
——以地域划分,将关中分成三块地区;
右扶风、左冯翊、京兆尹——一听名字就知道,这三个职务管的是哪片儿地方。
改中尉为执金吾,则是通过更改职务名称,明确原中尉属衙被分离出来的事实,同时又明确指出‘新中尉’的职责:皇帝手里的棍棒,谁不听话就锤谁。
再将大农令改名为大司农,并使其取代原本的内史,彻底颠覆原内史属衙‘关中小丞相’的政治属性;
使‘新内史’:大司农,成为权力覆盖面积遍布天下,却并不大包大揽,只专精农业事务的、真正意义上的‘治粟’官。
这,才是刘荣认为有必要、有积极作用的九卿改制。
还是那句话:要改,你就去改他的职能,然后再根据新职能,考虑是否要换个新名字。
所以,拆分内史为右扶风、左冯翊、京兆尹,改中尉为执金吾,改大农令为大司农,并使其取代原内史,刘荣都打算照抄历史作业。
——因为即便刘荣作为穿越者,也想不到比这更出色、更合适的内史拆分方案。
而其他的部分,纯纯就是闲着没事换个名字玩儿,完全没有实际意义的‘改制’,刘荣就敬谢不敏了。
“如此一来,新三公,便是丞相、御史大夫、御史中丞。”
“御史大夫,御史中丞——都带个‘御史’,倒是可以给其中一个改个名字,以作为区分。”
“嗯……”
“司空?”
“亦或是……”
只思考了片刻,刘荣便否定了这个选择,却也下定了给御史大夫、御史中丞其中一个位置换个名字的决心。
而且最终改的,大概率会是御史中丞。
原因很简单:御史大夫无论改或不改,大家都知道他是三公之一的亚相。
但御史中丞,百十年来都是御史大夫底下的一个小弟,即便刘荣盈给抬上三公之列,也难免会被人所轻视。
所以,刘荣打算给御史中丞,换一个‘更像三公’的名字。
至于为什么否定‘司空’的备选,则是因为司徒、司空、司马,并非三百多年后的汉末三国才有,而是早在数百年前,就已经被明确记录在《尚书》当中的古三公。
其中,司徒对应如今的丞相,司空对应当下的御史大夫,而司马,便对应过去百十年来的太尉。
既然已经决定罢设太尉,改以大司马取缔——尤其还将太尉大司马踢出三公之列,那司徒、司空这两个古称出现在三公当中,就多少有些不合适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