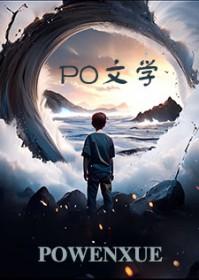366小说>朕这一生,如履薄冰 > 第390章 又一年秋(第3页)
第390章 又一年秋(第3页)
当然,相较于惩罚性质的所谓紧迫感,刘荣还是更倾向于奖励性质的鼓励。
比如:某个被绣衣卫谈查到的情报,在经过核实之后,针对搜集到该情报的个人和部门,进行包括但不限于金钱的奖励;
如此一来,哪怕是为了钱,绣衣卫上下也会认认真真的工作,而不是端着铁饭碗浑浑噩噩。
只是这件事,刘荣还需要考虑考虑。
还是那句话:相比起其他司法、行政机构,绣衣卫这样的情报部门,实在是太过于特殊。
他们很容易走上极端。
要么胡搞瞎搞,编排宗亲诸侯,要么彻底躺平,完全不作为;
在他们眼里,似乎永远都没有‘折中’这个选项。
所以,对于这样极端,而且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转变为另一个对立面的极端的特殊部门,任何措施,都需要慎之又慎。
——用金钱作为激励,鼓励绣衣卫更努力的工作,理论上是可取的;
但如何避免它们再次走上极端,生诸如‘绣衣卫为了奖励,编排朝中公卿酒池肉林’之类的离谱时间,还需要好生斟酌,并再三推敲。
换而言之,这件事,急不得。
但无论如何,过去这些年,压在绣衣卫上下心中的,那个名为‘说不定哪天就要下岗’的大石,却总算是落了地。
而绣衣卫,在刘荣眼中,其实还有一个比较致命的问题,是迫切需要解决的。
“过去这些年,绣衣卫上下用于查探情报、行贿宗亲诸侯左右的钱金,似乎都并非直接出自少府内帑?”
一听刘荣问起此事,周仁便当即明白过来:刘荣,是要针对绣衣卫混乱的财政系统,或者说是‘经费审批系统’动刀了。
故而,周仁并没有急于开口答话,而是低头思考了许久。
措辞一番,又组织好语言,周仁才将过去这些年,绣衣卫内部的大体运转模式娓娓道来。
“正如陛下所言,绣衣卫放出探子,无论是探子的衣食住行,还是行贿、交好,都需要不少钱、金。”
“这是一笔相当不菲的开支。”
“——就拿当年,吴楚七国之乱爆前距离;”
“当时,吴都广陵,便有绣衣卫分司一处,属绣衣卫者百五十,爪牙上千。”
“为了维持着千余人,在广陵城的情报搜集,以及针对吴王宫的查探,先孝景皇帝每年,就要赏赐臣不下五百金。”
“而这五百金,仅仅只是广陵一城所需。”
“余者——如赵都邯郸,齐都临淄,燕都蓟邑,楚都彭城等,用度虽少些,却也少不到哪里去……”
一听周仁这话,刘荣便算是明白过来,绣衣卫过去的经费,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获得、下了。
——直接由天子巧立名目,给指挥使:周仁降下赏赐;
再将这个赏赐作为项目经费,下到绣衣卫内部具体的部门,或是具体的个人手里。
如此一来,项目经费有了,朝堂内外却也不会因为一笔不明所以、说不清楚的额外支出,而对绣衣卫的存在有所察觉。
至于这么做的弊端,则正是刘荣方才,表示绣衣卫未来‘不能再完全藏在幕后’的原因所在。
——天子赏赐,尤其还是无缘无故的赏赐,一次两次还好,次数多了,指不定能出什么乱子!
好比周仁这个绣衣卫指挥使,先帝每年几千金的赏赐下去,别说是后世野史了——便是如今朝堂内外,都有人说郎中令周仁,是先孝景皇帝的老相好、好基友了。
偏偏刘荣还无从辩驳!
毕竟老刘家的皇帝,在这方面的名声向来不算干净。
所以,为了以后不被造黄谣,不被野史描述为‘和郎中令拼刺刀’的基皇,刘荣必须让绣衣卫,在一定程度上‘浮出水面’。
因为只有这样,绣衣卫才能得到一笔正常渠道的专项拨款,而非天子给予指挥使个人,再被指挥使偷偷用于绣衣卫运作的所谓赏赐。
再者说了:恩出于上!
绣衣卫这么个要害部门,经费明明出自天子,名义上却都是由指挥使‘自掏腰包’,这算个什么事儿?